【識港網訊】人稱「民國第一才子」的錢鍾書,自言不喜與人交往,更多次拒絕應酬,只愛與書為伴。個性冷靜尖銳的他,對後輩卻多有關心。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再復與錢鍾書生前亦師亦友,在錢鍾書作古後多年,才懷着稍為平伏的心情,寫下對前輩的追思之情。且看看曾被冰心譽為「我們八閩的一個才子」的劉再復,其筆下的錢鍾書的溫暖形象。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批評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讚揚他的文章。
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於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託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

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說:「你也當甚麼《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參乎?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儘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
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着說:「這回錢先生着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
* * * * * * * *
錢先生對《錢鍾書研究》一事如此認真的態度,絕非矯情。他的不喜別人臧否的態度是一貫的,他自嘲說:我這個人「不識抬舉」,這也非虛言。一生渴求高潔、安寧,確實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對「抬舉」之事怒不可遏,言語過於激憤。
一九九六年,我聽到法國的友人王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編輯)說,他看到國內報刊有一消息,說李希凡等人聯名寫了呼籲信,要求制止江蘇無錫把錢先生的祖居舊址夷為商場,以保護國寶文物。知道此事後,他就致函楊絳先生,詢問此事是否需要聲援一下。楊先生在回函中傳達了錢先生的話:「我是一塊臭肉,所有的蒼蠅都想來叮着。」一聽到這句話,我就相信這是錢先生的語言,別人說不出如此犀利透徹的話。難怪人家要說他「尖刻」。然而,這句話也說明他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寧與高潔是怎樣的不留情面。
* * * * * * * *
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複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
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頭髮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倖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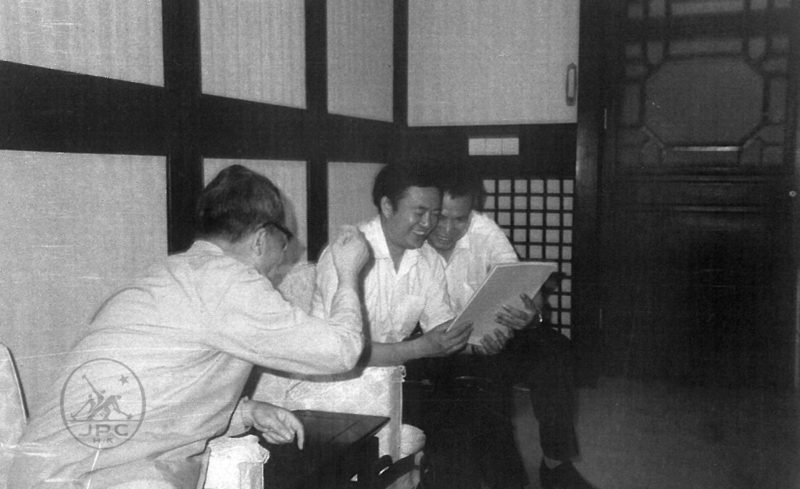
不過,出國之後,我悟出「頭髮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
* * * * * * * *
我和錢先生、楊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一九七三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幹校搬回北京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並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
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台之後,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裏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於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

* * * * * * * *
錢先生雖然整天埋頭著述,但頭腦非常清醒,他好像明白,我雖然當了研究所負責人,其實頭腦並不清醒,所以常常提醒我。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應邀將到美國五所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進行學術交流並作學術講演。錢先生除了託我把兩本《洗澡》(楊先生小說)分別交給夏志清先生和李歐梵先生,還叮嚀我說:你到美國這麼多學校,交往的人很多,一定要注意一點:只講公話,不講私話。剛聽錢先生的叮嚀,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這是錢先生給我的護身法寶。倘若破譯一下,就是要我言行端正,不可對任何人講迎合的話,拉關係的話,更不可講機密的話。在美國兩個多月,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錢先生「不講私話」的囑咐。
這一年的五月上旬,我因為趕回去參加社會科學院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因飛機的耽誤沒參加上)被捲入政治風波,於八月初又來到美國。在芝加哥大學落腳後,我給錢先生打了一次越洋電話。接電話的是錢瑗。她放下電話去找錢先生。大約三分鐘後,錢瑗說:父親讓我告訴你,在海外不要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政治不是我錢某能搞的,也不是你能搞的。
錢先生這一叮囑很認真,很鄭重。過了幾個月之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陳松齡先生告訴我,說他剛到北京去拜訪錢先生,一坐下來,錢先生就問,你們知道再復在海外怎樣嗎?接着又讓我們轉告你:在海外千萬不要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政治不是我們這些人能搞的。
錢先生不僅在學術上很嚴謹,在立身處世的態度和方法上也很嚴謹。絕不參與政治,這是他的堅定立場,也是他能夠給予我的最具體、最大的關懷。

_________________
上文節錄自〈錢鍾書紀事〉,收在劉再復所著的《吾師與吾友》。作者於書中憶述其二十多位「師友」,他們大都是名師大家,包括錢鍾書、夏志清、胡喬木、周揚、胡繩、施光南、聶紺弩、馬思聰、高行健、金庸、李澤厚等等。通過作者一字一字的記敘,引述往來之書信內容,緬懷亦師亦友的深刻情誼,文人形象與情思躍然紙上。讀者不獨感受到作者對多位師友的真摯情感,同時讀到富有史料價值與文獻意義的珍貴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