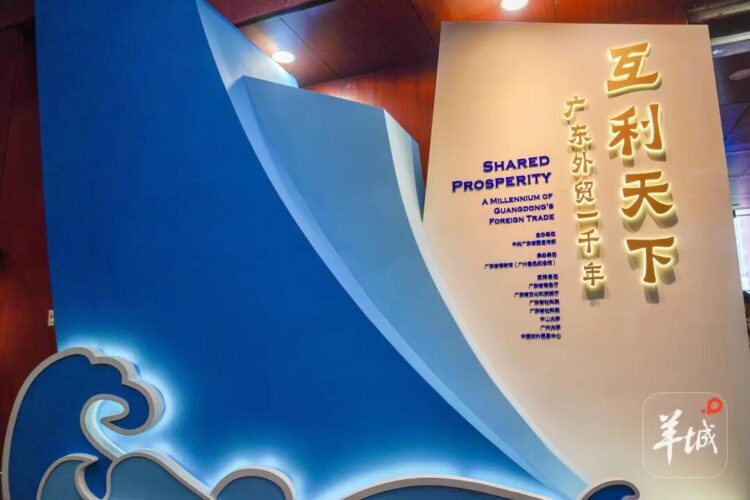
【識港網訊】 10月31日,第138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第三期開幕迎客,廣州琶洲展館内熙攘往來。
就在幾公裏外的廣東省博物館裏,「互利天下:廣東外貿一千年」大展正在熱展,不斷吸引着參與廣交會的海外客商和各界市民、遊客前來參觀。
古今外貿的活力在此刻跨越時空,交相輝映。當我們走近這一件件跨越唐宋元明清的文物遺存,更加清晰地解鎖了廣東從「海上絲路起點」躍升爲「中國外貿第一大省」的深層邏輯。文物背後的曆史故事與制度沿革,正爲當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曆史鏡鑒。
唐代:制度剛性與人文溫度
走進展覽現場,入口不遠處一枚不起眼的伊娑郝銀铤拓片便引起了不少遊客的興趣。
「第一次知道唐代就有這麽細緻的外商治理,連外商遺産的處置都考慮周到了!」來自廣東實驗中學的伍同學看到這枚銀铤背後的故事頗感意外,「在這個展覽裏,我看到了曆史教科書裏都沒有寫到的很多故事和細節。」
唐代的廣東,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而這枚伊娑郝銀铤,便見證了唐代對外貿易治理既以制度爲綱,又不失溫度的智慧。
公元8世紀下半葉,波斯商人伊娑郝來華貿易期間,不幸客死廣州,因三個月内無親屬認領遺産,嶺南節度使與市舶使依例對他的遺産移送長安。
這一史實背後是唐代針對外商遺産處置逐漸成熟的管理制度,既保障外商合法權益,又通過官方介入維護貿易秩序。
一方面,官府并非在外商去世後立刻處置遺産,而是設定了三個月的認領窗口期。這一期限的設置,充分考慮到古代交通不便的現實,外商親屬可能遠在波斯或其他海外地區,需跨越山海才能抵達。另一方面,官方主動介入保護而非放任,從根源上防止了本地豪強或不法之徒侵吞、霸占外商遺産,用公權力爲「異鄉人」築起權益屏障。
安史之亂後,外貿事務由地方軍政長官(嶺南節度使)與專職外貿官員(市舶使)協同共管,節度使負責封押、護送,市舶使負責估價、登記,形成「分工而不割裂」的治理格局。
此外,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繁榮,多有蕃商留居。族群複雜、數量龐大的蕃商在廣州并沒有處于無序狀态,而是在城西開始逐漸形成蕃坊。
中國著名曆史地理學家曾昭璇在《廣州曆史地理》中寫道:「唐代蕃坊是一個外國商人聚居區,不是一條街。北到中山路,南達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城牆),東達解放路。」
唐代對蕃坊的管理更體現出尊重包容的智慧,允許外商聚居形成 「蕃坊」,由 「蕃長」自主約束内部事務,既尊重外商的文化習俗與生活方式,又将貿易活動納入官方管理框架,實現「多元共生」與「秩序穩定」的平衡。
如今,當代中國持續完善外商投資法、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保障外資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争,正是對唐代「制度化包容」理念的傳承與發展。
宋代:從短期交易走向長期共生
南海神廟對廣州本地市民遊客來說頗爲熟悉,但展廳裏《大宋新修南海神廣利王廟之碑》的拓片卻講述了「老廣」們都不一定知道的故事。
因陸上對外貿易範疇受限,宋代中國遂将外貿重心轉向海路。由此,北宋攻克南漢後随即在廣州設市舶司,廣州是宋朝對外交往的唯一港口。
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頒布的《廣州市舶條》,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貿法,後推廣至全國各市舶司。
廣州市舶司不僅成爲北宋首個市舶機構,更憑借「管理範圍最廣、存續時間最長」的特點,爲當時的廣東乃至全國外貿提供了長期穩定的制度環境。「市舶宴」便是其中的點睛之筆。
曆史學家蔡鴻生曾在羊城晚報撰文《市舶宴:宋代廣州爲外商踐行的酒會》。文中指出,因受季候風制約,宋代來往廣州的海舶「冬往夏歸」,許多外商需在廣州居住一整年(稱爲「住唐」),待來年季風來臨時再啓程。每當外船啓碇前,廣州市舶司提舉官便會設宴請客,以公使酒庫的酒爲外商餞行。
本次大展的策展團隊特别在展廳呈現的《宋會要輯稿》亦能佐證。據其記載,宋政府積極采取優待蕃商政策、定期設市舶宴等,鼓勵他們來廣州貿易。外貿管理人員中外兼有,體現出對外貿易中外共參的特點,更以「柔遠」之道吸引外商,促進中外友好,維護國家穩定與繁榮。
宋代的廣東外貿,通過「體系化制度保障貿易秩序、人文性禮儀增強外商認同」的雙重舉措激活貿易活力,讓外貿從「短期交易」走向「長期共生」。
而宋代「市舶宴」,不再局限于「完成基礎服務」,而是通過「主動關懷」讓海外客商感受到被重視,進而增強對廣東外貿環境的認同與信任。
這種「剛柔并濟」的思路,既是千年外貿智慧在當代的鮮活轉化,也爲中國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了可借鑒的「廣東樣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太宗開始,宋朝中國曾遣使臣團赴海外諸國,主動招徕商賈來華貿易。此後,曆朝君主及地方州府亦多次循此舉。可見,宋代并未止步于繼承唐代市舶制度,更推出「優待蕃商」的主動政策,将外貿管理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招引」。
元代:跨文明技藝融合與「需求定制」的外貿突破
在展廳中間,廣東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元代青花人物圖玉壺春瓶被放在獨立的專門展櫃中,瓶身上看似傳統的器型與紋飾,卻藏着跨文明融合的密碼。
展覽策展人丁蕾在展櫃前向記者解讀這件國寶:首先燒制青花瓷所用的钴料,并非中國本土出産,而是來自波斯地區,促成了中國瓷胎與波斯钴料的技藝融合。
曆年來,廣州城市中心及沿海沉船中發現的大量青花瓷器碎片,均證實廣東是元青花外銷的重要樞紐,各地瓷器經廣東港口或沿海運送至海外,推向全球市場。
實際上,元青花的誕生直接源于海外需求的驅動。古波斯信奉的伊斯蘭教法典《古蘭經》禁止使用金銀餐具,中國瓷器的精緻與實用恰好填補了這一需求空白,而爲适應伊斯蘭國家「席地圍坐」的飲食習慣,當時的中國工匠們專門燒制大罐、大盤、大瓶等大型器皿,方便多人共享。
「當時元代的廣東商人就能想到定制化設計,實在太巧妙了。」從事家居外貿的觀衆趙女士是本次廣交會的參展商,她也來到這個展覽。「我們現在給海外客戶做定制家具,其實也是這個思路。從規模化轉向精準對接需求,這是元代的廣東就驗證過的路。」趙女士說。
元代的廣東外貿以「精準對接海外需求」爲核心,通過跨文明的技藝融合,打造 「定制化産品」。這一思路爲我們當代廣東外貿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提升」、實現價值鏈升級提供了曆史啓示。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政府對瓷器海外貿易有着直接的扶持與參與,在瓷器出口貿易商采取不少支持措施,尤其是在稅收上施行讓利優惠政策,注重遵循互通有無、平等公平、自願買賣等具有契約精神的文明規則。
明代:卻金不受與通關便利
展覽現場,展出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代東莞「卻金亭碑」的碑文拓片。上面記載了一段廉政佳話:嘉靖十七年(1538年),番禺知縣李恺奉命主持東莞外貿稅收(「榷莞稅」)。
李恺大刀闊斧改革,允許外商自報貨物數量,簡化查驗流程,明确「不封船、不抽稅、不拉差役」,嚴禁官吏随意騷擾外商。曾因當地官員勒索而苦不堪言的外商大爲受益,爲表謝意,暹羅(今泰國)商人柰治鴉看邀集外商籌銀百兩相贈,李恺堅決拒收。
李恺的改革還将信任賦予外商,既提升通關效率,又降低貿易成本,與唐代市舶司 「閱貨抽分」的規範化傳統一脈相承。
崇祯《東莞縣志》(卷六)對此事也有記載:「李恺以嘉靖十七年莞榷稅,分毫不染,彜人請于藩司,崇坊以報德,乃建卻金留芳亭于莞教場。」珍貴的卻金亭碑一直保留至今,碑記講述了這段佳話。
幾位來自東莞的觀衆看到《卻金亭碑記》拓片,格外親切。「卻金亭碑是我們東莞的佳話,沒想到在省博外貿大展上還能看到它。」市民周女士說,「李恺的改革讓外商信任東莞,現在東莞外貿這麽強,也是繼承了這份誠信底色。」
明代對外貿易制度以國家安全與政務穩定爲核心,海禁政策與朝貢體系貫穿始終。廣東作爲海上門戶,在服從中央管控的同時,亦不斷探索地方路徑,成爲制度變革的先行者。
明中期後,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躍,以生絲、絲織品等商品推動貿易格局轉型。廣東率先推行「廣中事例」,稅收上複用宋元時期的抽分制,萬曆年間又改爲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亦顯著增加外貿收入。
此外,廣東允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允許百姓與外商直接貿易,展現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彈性空間的智慧。
這一過程不僅體現地方因勢應變的能動性,也爲當今複雜國際環境下推進區域合作、靈活開放提供了曆史借鑒。
從明代的自報核驗、到「廣中事例」的大膽創新、積極探索,再到當代的便捷通關,制度創新、互利互信始終是廣東外貿穿越周期的核心動力。
清代:從商品輸出到文化共鳴
乾隆廣彩漿胎花卉獎杯紋瓜棱扁瓶在柔和燈光的照射下,瓶身上「C」形「S」形的洛可可曲線顯得優雅唯美。暖黃色的光線漫過玻璃展櫃,襯得瓶身愈發溫潤,精緻得仿佛能觸摸到細膩紋理。
不少年輕女生拍照打卡這件充滿西方審美趣味的獨特瓷器,「沒想到幾百年前的廣東就有這麽‘潮’,廣彩不愧是以前‘中國制造’的全球爆款。」
乾隆廣彩漿胎花卉獎杯紋瓜棱扁瓶處處透着「洛可可」風格的精緻,大量的優雅曲線與貝殼狀紋飾,迎合了18世紀歐洲的審美潮流。同時,這類瓷器還常常融合中國傳統的花鳥紋、嶺南風物元素等,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獨特氣質。
從傳統的茶葉、絲綢、瓷器到外銷畫、牙雕等外貿商品,清代廣東的外貿早已超越「生活器具」的範疇,實現從「商品貿易」到「文化共鳴」的躍升。
從波斯商人伊娑郝客死廣州後官府依規處置遺産,到宋代市舶司設宴爲「住唐」 蕃商餞行;從元代中東钴料與景德鎮瓷胎碰撞出元青花的驚豔,到明代暹羅商人與東莞官民因「卻金不受」結下互信;再到清代廣彩瓷器擺上歐洲宮廷的餐桌,「中國風」成爲歐洲社會的流行風尚……
千百年來,廣東外貿始終朝向「互利天下」的最高境界:不僅交換商品,更交換審美與文化,以國家制度參與保障,讓不同文明在共鳴中相互融合接納。
貫穿始終的,是「互利共赢」的主旋律。這份主旋律,讓「東西南北中,發财到廣東」的共識穿越時空,成爲外貿行業對廣東最深刻的認同,更讓廣東外貿跳出 「物質交易」的局限,成爲不同文明對話的橋梁、共生的紐帶。
我們始終懂得,真正的「互利」,從來不是一時的數字增長,而是跨越國界的信任傳遞;真正的「開放」,從來不是單向的商品輸出,而是文明間的雙向奔赴、長久共生。這既是廣東外貿「互利天下」的千年答案,也是它面向未來的永恒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