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港網訊】我剛開始寫這本書時,覺得這本書應該會談怪獸與創意,談女性藝術家要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這是我告訴出版社這本書所要談的內容。但我重新從奧菲爾的脈絡來閱讀〈女性的職業〉,這次讀過倫納德(Leonard Woolf)於吳爾芙逝世後出版的修訂版之後,明白自己忽視了文中非常重要、實際上可謂文中高潮的一段話。吳爾芙比喻創作過程如同「女性漁人」那樣,將她的文字拋到想像力的深海裡,任其在「我們無意識深處的每塊石頭和裂縫中遨遊」,隨著文字漂泊、想法流動,出現了吳爾芙認為「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常遇到」的某些東西:
發生了碰撞與爆炸,浪花翻騰、出現錯亂。想像力撞到了某種堅硬的東西。⋯⋯她想到某件事,與身體有關的事,想到她身為女人,並不適合表達這種激情。⋯⋯她寫不下去了,發呆時間結束了。
上述那段崩潰的過程變成自我審查的寓言——阻斷女性藝術創作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小孩或先生,而是內化的警告聲音:注意!注意!我們已踏入水深危險之處!吳爾芙在文章最後,回到一開始演說中談的議題:女人的工作與性生活,並視之為她作家生涯中的兩大關鍵挑戰。「首先——殺死『家中天使』——我認為自己已完成這任務,她已經死了。但其次——以我自己作為主體,說出自己感受到的經驗——這我應該尚未辦到,也不相信有任何女人已成功做到。」
就是這個:這或許就是藝術怪獸試圖要做的事情。雖然她已殺死天使,但仍有東西在阻礙著她。她想說一些事,卻受到社會制約而說不出口。截至目前為止,藝術怪獸相關的論述大多在談女性藝術家的生活,但瞭解他們的作品也很重要,看看她們一心想做的事情為何,為何為此甘冒被稱作怪獸的風險。
吳爾芙認為,我們後續該做的,是鼓起勇氣重塑社會灌輸的文化傳統,並以體化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作為主要媒介。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勸勉女性作家,若要創作出真正屬於自己、不受天使干預的作品,就必須打破「句子」,接著打破「順序」。我們必須從中理解到的是,此處談的不僅是女人,而是每個在文法規範之外的人:此即怪獸的另一個定義。吳爾芙追求的,與《燈塔行》的小說接近結局之處的描述很像,莉莉努力透過她的畫傳達的是:「美麗的圖像。美麗的語句,但是她想捕獲的是那神經上的顫動,那還沒有被變成任何東西的東西。」演說版的〈女性的職業〉以較為原始、急迫的方式呈現這些概念,吳爾芙在這版本中,明確地將想像力人格化,其實就是賦予想像力一個身體,使其能夠衝刺、躍入「天知道在哪裡的」深處,但她卻必須「氣呼呼又失望地」被拉回來。「『親愛的,總而言之你做得太過分囉。』女性漁人告訴她。 她試圖安撫不滿的想像力,她保證『情況絕對不會如此』。總有一天,男人聽到女人『真實談論她的身體』時,不會感到那麼『震驚』。只要等五十五年左右,五十五年之後,我就可以運用你可以給我的那些古怪知識。但現在不能。」「很好,」想像力如此說,穿回她的襯裙和裙子,「我們會等。我們會再等五十五年,但我覺得這樣似乎太可惜了。」
1975年,距離吳爾芙的演說還不到55年,藝術家卡洛琳.史尼曼爬上紐約東漢普頓一間美術館的桌子,既未穿襯裙,也沒穿裙子。事實上,她身上除了一件漂亮的小圍裙之外,幾乎衣不蔽體,而且很快就把圍裙脫了。她把深色顏料塗在身上,打開一本自己寫的獨立刊物開始朗讀,擺出各種模特兒的姿勢。接著把書放下,兩腿張得更開,從陰道拉出一個捲軸,有點像臍帶,是厚厚的螺旋狀,開始大聲念:
我遇見一個開心的男人 一位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
他說我們很喜歡你
你很有魅力
但別叫我們
看你的電影
沒辦法
有某些片
我們無法看
像是雜亂的個人式作品
像是堅持談感受的
像是有手摸觸感的
像是放縱的心情日記
像是混亂的畫風
像是難懂的格式塔(gestalt)
像是原始的技巧
有人認為史尼曼說這段話的對象,應該是她當時的伴侶安東尼.馬柯爾(Anthony McCall),他的確也是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但她1988年告訴電影史學家史考特.麥克唐納(Scott MacDonald),那段獨白的對象其實是《藝術論壇》(Artforum)的評論家兼編輯安妮特.米切爾森(Annette Michelson),一位「沒辦法看她的電影」,在紐約大學上電影課時也未將其納入教學,並將她的作品排除於女性主義經典之外的人。這當中有許多米切爾森談到史尼曼時告訴學生的話,如「像是混亂的畫風」、「像是有手摸觸感的」、「像是放縱的心情日記」。 這幾句話建構的女性主義藝術家宣言在字裡行間顯然地,恰好是吳爾芙的天使禁止她寫下的內容。女性主義者用盡心力要使自己的身體獲得解放,〈內在捲軸〉(Interior Scroll)將那一刻具體表現出來,創作出向前後左右延伸,聚集了所有的美與溢踰(excess),閃耀出光芒的藝術。
史尼曼說:「我原本不想從陰道拉出捲軸當眾朗讀」。但她嘗試「公開」這文化想要「壓抑」的內容時,人們卻大為驚駭,使她認為有必要如此做。史尼曼想透過〈內在捲軸〉,「以有形的方式,將無形的、被邊緣化與嚴重受到壓抑的外陰歷史表現出來。外陰十分強大,能帶來欲仙欲死的快感,使人能夠分娩、帶來轉變、產生月經,也能使人成為母親,藉此來證明那不是死的、看不見的地方。」 史尼曼使女性身體能夠吐露以前沒有管道可說出口的話,〈內在捲軸〉使「外陰空間」變得清晰與可見,使其除了擁有潛在的生育能力之外,也極具創造力。史尼曼2019年過世時,我將她的照片發布於社群媒體Instagram紀念她,卻被該平台下架。
史尼曼本應別無所求,自她開啟藝術家生涯以來,作品就經常因為敢於描繪某些內容而遭到審查與抨擊,她就讀大學時找不到裸體模特兒,所以找裸體熟睡中的男朋友下手,畫他鬆軟的陰莖,也畫自己沒有穿衣服的樣子,因此遭到退學;展館總監薩賓.布萊茲維澤(Sabine Breitwieser)表示:「但她為同為畫家的男同學擔任裸體模特兒時,卻未曾遭到任何人反對。」她一九六三年的攝影集《審視身體》(Eye Body)中收錄陰蒂的照片時,藝術界對此相當反感。「為何要在藝術界做這件事,不去『色情』界做呢?」他們說這是淫穢的、是春宮 圖,也說這與藝術毫無關連。
「淫穢」一詞的英文是 obscene,詞源是ob-(意指:前面)與 -caenum(意指:污穢)。淫穢使我們置身於應該要被洗掉或隔離起的污穢面前,按瑪利.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潔淨與不潔的定義,就是「不合宜之物」,女性私密的身體部位在藝術界即屬於不合宜之物。
1991年時,史尼曼發表了一篇極具真知灼見的文章〈淫穢的身體/政治〉(The Obscene Body/Politic),談的是身體、淫穢、以及專業水準與性別歧視。她寫道,若女性早在數十年前就闖入了藝術界,必然是出於她們過去數千年來當藝術家時遭到排擠的憤怒:藝術界不使用稱呼她們的代名詞,「而是以男性的他稱呼」,並以性化、「戀物」角度看待她們,同時又將她們真正的身體視為「污穢、糟糕、毒害人的」。史尼曼在1990年代一部談女性藝術家的紀錄片中,於〈維納斯對鏡梳妝〉(Rokeby Venus)這幅畫出現於螢幕上時以聲音說道:
自古至今我都只能出現在畫布上,事實上,就像被埋葬成為一幅圖畫,在一個除了他這個代名詞(無論是指藝術家還是學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代名詞擁有權威的文化中,我真的不知如何理解「自己既是真實能夠做畫的人,但身體又成為描繪對象」。
身兼藝術家與藝術的史尼曼說道:「女人只要作風夠像男人,創作時明顯走在男人開闢的傳統與道路上,就能挑戰並威脅到允許她們加入男子藝術俱樂部(the Art Stud Club)一脈相承的精神領域權力。」史尼曼如同其他70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藝術家,希望能夠受到重視,但她更認真從自己的性別與身體角度來提出挑戰。她在行為藝術〈赤裸行動演說〉(Naked Action Lecture, 1968)中一邊脫衣服,一邊用幻燈片進行藝術史的演說。
推薦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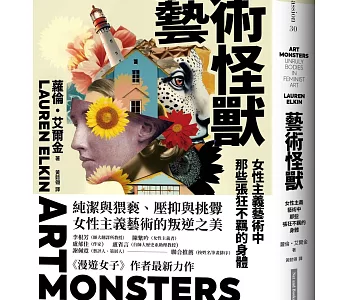
《藝術怪獸:女性主義藝術中那些張狂不羈的身體》
作者:Lauren Elkin
譯者:黃懿翎
出版社:網路與書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