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下是貓,名字嘛,暫且還沒有。
要說在哪兒出生,我沒有絲毫的印象,只記得曾在幽暗潮濕的地方喵喵地哭過。就是在這裡,我第一次遇見了人這種東西。後來才聽說,書生是其中最為猙獰的種族。據說書生常常把我們捉去,煮了吃掉。那時候我一無所知,所以並不覺得特別害怕。只是被他托在掌上嗖地突然舉高時,感覺飄飄悠悠。當我在他手掌上定下心來,看見了書生的臉,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人類。奇怪的感覺至今仍記憶猶新。首先,理應有毛來裝飾的人臉光溜溜的,像個燒水壺。後來我也遇見很多貓,從未見過這麼不完美的臉。而且,他的臉部中央過於隆起,洞裡面不時地噗噗地躥出煙霧,嗆得我受不了。最近我才弄明白,那是人類吸食的煙草。
我在書生的手掌上舒舒服服地坐著,沒過多久便飛速旋轉起來,也不知道是書生在動,還是我在動,只覺得天旋地轉,噁心難受。剛尋思這下沒救了,啪的一聲,我眼冒金星。之前的事我還記得,後來發生了甚麼卻怎麼也記不起來了。
當我回過神來,書生已經消失不見。兄弟姐妹們一隻都見不著,連最最重要的媽媽也沒了蹤影。而且,現在我身處前所未有的明亮之處,亮得幾乎睜不開眼睛。咦,真奇怪。我慢慢爬出來,渾身疼痛。原來我被書生突然從稻草窩扔進了矮竹叢。
好不容易爬出竹叢,前面是一個大池塘。我坐在池塘前面,琢磨接下來咋辦,卻沒甚麼好主意。過了一會兒,我尋思著如果哭鼻子書生或許會來找我,試著喵喵地哭,可是不見人來。這時候風聲唰唰,吹過水面,天開始黑下來。我肚子很餓,想哭也哭不出聲。沒轍,只好先找個能填飽肚子的地方。拿定主意,我邁步慢騰騰地繞著池邊向左走,步履很艱難。忍著痛往前爬,總算到了有人味的地方。天無絕貓之路,我鑽過竹籬笆的破洞,來到一戶人家的院子裡。緣分真是奇妙,如果竹籬笆沒有破,我也許就餓死在路邊了,常言道,一樹之蔭,前世之緣,此言不虛。這個籬笆洞現在已經成為我拜訪鄰家三色貓的必經之路。話說我進了這戶人家,不知接下來該怎麼辦。天已經黑了,飢腸轆轆,天寒地凍,眼看就要下雨,容不得半刻遲疑。走投無路之下,去暖和亮堂的地方再說。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已經鑽進人家裡了。在這裡我有機會遇見了書生以外的人類,碰到的第一個人是廚娘,她比之前的書生還要粗暴,一看見我就揪住脖子扔到門外。完了,我心想,兩眼一閉聽天由命算了。可是又冷又餓,怎麼也扛不住。我乘她不注意,爬進廚房。沒多久,我又被扔了出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記得如此這般重複了四五次。那時候,廚娘也厭煩了。對了,前些時候我偷吃了她的秋刀魚,總算報了仇,大快我心。她正要把我丟出去的當兒,這家主人出來了。「吵吵鬧鬧的,怎麼回事啊?」廚娘提溜著我,說這隻流浪貓怎麼趕都要進廚房,不知咋辦。主人捻著鼻子下面的黑毛,打量了一下我的臉,說了一句「那就把它收下吧」,轉身進了裡屋。貌似主人平時話不多。廚娘不情願地把我扔進廚房。就這樣,我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容身之處。
我家主人很少和我照面。聽說他是教書的先生,從學校回來便成天待在書房裡,幾乎不出來。家裡人都覺得他勤勉好學,他也擺出一副讀書人的架勢。其實他並非家人所說的那樣用功,有時我躡手躡腳往書房裡窺視,見他常在午睡,口水流到讀了一半的書上。他的胃長期病弱,皮膚呈淺黃色,顯得沒有彈性,缺乏活力。奇怪的是他飯量很大。飽食之後喝助消化的澱粉酶,然後展卷讀書,讀上兩三頁便犯睏,口水流到書本上——這就是他每晚重複的功課。我雖然是貓,有時也想,教師這職業真是輕鬆。如果投胎為人,最好是當教師。如此呼呼大睡也算工作,連貓都不難做到。可是主人說,沒有比做教師更辛苦的職業,每當朋友來訪,他總是怨聲連連。
剛住到這戶人家時,除了主人,我極不受人待見;不管去哪裡都遭冷遇,沒人理我。我現在還沒取名,可見我多麼不受重視。別無他法,我只好盡量多待在收容我的主人的身邊。早晨他讀報,必定坐在他的大腿上;他午睡時必定趴他背上。並非主人喜歡這樣,而是除他之外沒人搭理我。後來我有了經驗:早晨躺在飯桶上,晚上趴在被爐上,天氣好的時候睡在檐廊上。最舒服的還是到了晚上鑽進小傢伙的床鋪裡,小傢伙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晚上在一間屋子裡共睡一床。我總是尋找空隙,見縫插針鑽進他們之間。運氣糟糕的時候,其中一人醒過來,那就糟糕了。兩個小傢伙——小的那個尤其壞——深更半夜也不顧忌,嚎著貓來了貓來了,放聲大哭。我那神經性胃病的主人一準被吵醒,從隔壁房間飛奔過來。事實上,前些時我的屁股剛挨過尺子。
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觀察得越多,我越發堅信他們任性自私。我時常同衾共枕的小傢伙更是過分。隨心所欲的時候把人家倒垂著提溜起來;往頭上套口袋;拋來拋去;或是塞進竈台裡。而我只要稍加反抗,全家人便追趕我大加迫害。前些時候我在榻榻米上磨磨爪子,太太就大發雷霆,從此不輕易放我進房間。就算我在廚房的木地板房間打顫也不理我。每當遇見斜對門家我所敬重的小白,她都抱怨沒有甚麼比人類更不懂人情。小白前些天剛生了四隻毛球般的小貓,出生後第三天,四隻小貓全被那家的書生扔到屋後的池邊去了。小白流著淚告訴我事情的原委,我等貓族必須為了天倫之樂、美滿的家庭生活而同人類戰鬥,剿滅他們,小白說。她說得極有道理。隔壁的三花貓也十分憤慨,人類並不明白何為所有權。原本在我們貓族,不管是小魚乾串兒的魚頭,還是鯔魚的魚扣,誰先發現就有權享用,其他的貓不遵守這個規則甚至可武力解決。可是那些人類絲毫沒有這等觀念,我們發現的美食總被他們強奪。他們靠強力搶去我們應得的食物,還毫不在意。小白住在軍人家,三花貓的主人是律師,而我住在教師家,相比之下我的生活更為樂觀,只需一天天湊合度日。人類再厲害,也不可能一直強盛下去,且耐心等待屬於貓的時代到來吧。
既然想到任性自私,索性說說我家主人因為任性而吃的苦頭吧。我家主人原本就沒甚麼過人之處,卻又凡事好嘗鮮。你看他,寫俳句投稿《子規》,新體詩投給《明星》,寫些錯誤百出的英文,有時又練練弓箭、學學謠曲,還吱吱嘎嘎拉過小提琴,可惜的是,沒一件學成的。明明胃不好,學起東西來卻格外起勁。在茅廁裡唱過謠曲,被人起了個「茅廁先生」的綽號。他倒毫不在意,翻來覆去唱那句「吾乃平家宗盛是也」,到後來大家一聽就想笑,「瞧,宗盛又來了。」我家主人也不知出於甚麼考慮,我住進來一個月之後,領當月薪水的那天,他提著一個大包匆匆忙忙回家,我正好奇呢,原來是水彩畫具、毛筆和「瓦特曼」畫紙。看起來他要放棄謠曲和俳句,開始畫畫了。果然,從第二天開始,他連著好幾天在書房裡畫畫,連午睡都不睡了。可是他畫的是甚麼,沒人能加以鑒定。大概他本人也覺得不怎麼樣,有一天,研究美學的朋友來訪,於是有了下面一番對話。
「我總也畫不好,看別人的畫沒甚麼感覺,一旦自己握筆才真正覺得難呢。」這是我家主人的感歎,的確,此話倒是不假。他的朋友透過金邊眼鏡打量主人的臉,「剛開始誰都畫不好呀,別的且不說,在室內憑想像根本沒法畫畫。想當年,意大利大畫家安德烈·德爾·薩托說過,畫畫必先摹畫自然之物。天有星辰,地有露華,上有飛禽,下有走獸,池中游金魚,枯木棲寒鴉,自然即為一副活的畫卷。要想畫得像模像樣,你先練練寫生吧。」
「是嗎?薩托這麼說過?我頭一回聽說。說得好,是這個道理。」主人一個勁兒地贊同。這時,金邊眼鏡後面閃過一絲嘲笑。
第二天,我和往常一樣,躺在檐廊下舒舒服服地午睡。主人破例從書房出來,在我背後忙個不停。我已經醒了,眼睛瞇了一分寬的細縫,看他到底在做甚麼。他正專注於安德烈·德爾·薩托呢。我見狀不禁失笑。朋友的調笑奏了效,他先拿我來練筆。我已睡足了,忍不住要伸懶腰。可是難得主人這麼專注地畫畫,我動身子就太對不住他了。我努力忍著,他畫好了我的輪廓,正在給臉部上色。老實說,作為貓我長得並不出眾,背脊、毛色和臉蛋都不如其他貓兒出色,但是長得再怎麼寒磣,也絕不是他畫的那副奇怪模樣。別的先不說,顏色就不對,我的膚色像波斯貓,淺灰中帶著黃色,點綴著生漆色的斑紋。這一事實毋庸置疑。可是看主人塗的色彩,不黃不黑,非灰非褐,也不是以上顏色的混合色。這顏色只能說是一種顏色,無法做出其他評價。更不可思議的是沒有畫眼睛,不錯,我是在睡覺,這樣寫生倒也沒錯。可是連眼睛的存在都無法分辨,也不知道是瞎眼還是睡著。我暗想,再怎麼聽從安德烈.德爾.薩托,這樣子也全然不行啊。不過,熱情還是可嘉得很。我想一動不動配合主人,可是剛才尿意就很濃,感覺全身肌肉都在發癢。在這刻不容緩的當兒,只好先失禮了,我撐直兩條前腿,低低地伸長脖子,打了個大大的哈欠。
____________
上文節選並改編自《我是貓(首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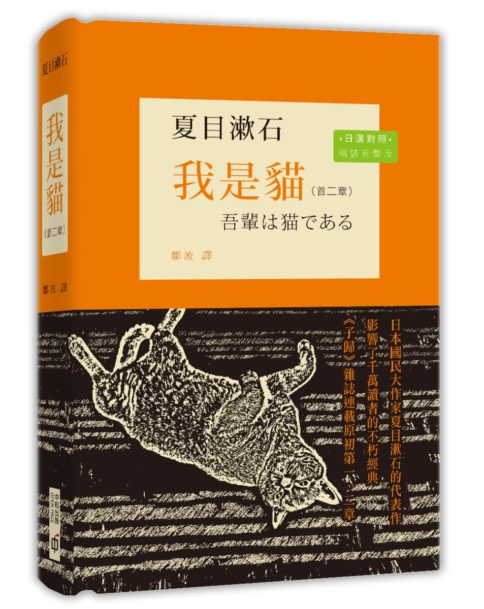
《我是貓(首二章)》
作者:夏目漱石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4/24/01014720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