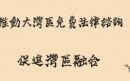【識港網訊】在旁觀者看來,蔡元培的一生,可備稱述的事件不少:少為才子,以「怪八股」科試聯捷,成進士,點翰林;戊戌政變後,在上海加盟光復會、同盟會,成為雙料革命黨,名列「民國四老」;作為民國第一位教育總長,他是孫中山臨時政府的內閣成員;中國第一個國家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長……但所有這一切,若比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輝煌來,似乎陡然顯得暗淡無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漱溟於四十年代即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紀念蔡元培先生》)換言之,正因為蔡元培執掌北大的成就非同尋常,對於中國現代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才使得他其他方面的工作變得微不足道。將近半個世紀以後,梁氏依然持此論,不過在論及蔡元培在北大的一段歷史意義時,更說出了這樣有些駭人聽聞的斷言:

今天的新中國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肇啟於五四運動。但若沒有當時的北京大學,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出現;而若非蔡先生長校,亦即不可能有當時的北京大學。(《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
如此將蔡元培與「新中國」直接掛起鈎來,多少給人以共和國的締造者的印象,結論自然突兀,但其中的蔡元培—北大—五四運動三者關係論斷,卻大致可信。較為準確的描述,還是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之一許德珩的話:「發動五四運動的主力是北京大學,而其精神上的指導者是蔡元培。」(《弔吾師蔡孑民》)

不管怎麼說,談論「五四」繞不開北大,談論北大又繞不開蔡元培,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蔡元培與「五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蔡元培於民國五年冬到了北京大學。1917年,蔡元培正式走馬上任。此時的北京大學,雖然早已由原來的京師大學堂改名,但本質並無甚麼改變,學校像個衙門,教師中有些本來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學無術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學生中也不乏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獨對讀書無興趣者。因為不少師生常到「八大胡同」的妓院去尋芳獵豔,與參議院、眾議院齊名,所以被稱為「兩院一堂」──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對於北大這種烏煙瘴氣的腐敗氛圍,蔡元培當然不會不知。上海的許多朋友,也力勸他不可就職,恐整頓不了腐敗,反而毀掉自己的名譽。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知難而進的險途。這多少有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陀精神。
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並以此為不二法門改造北京大學,在極短的時間內,奇跡般地將這所「官僚養成所」式的半衙門機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這在當年與當下,談論的人與文章都很多,似乎已成了共識。由於兼容各路人才,並包各種學說,保守派、維新派與激進派在北大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時代的重演。所以蔣夢麟說,蔡元培就是古代老哲人蘇格拉底,有了蔡元培的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羅家倫也說,北大精神以及「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實多受益於蔡元培—其實,早在「五四」當年,黃右昌教授就在蔡元培回校復職的歡迎會上點明「校風往往隨校長為轉移。北京大學現有博大純毅之校長,故博大純毅之校風,已見端倪」。可以說,延續至今的北大之傳統與精神,乃是在老校長手裡得以鑄塑並確立的。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業績在在存人耳目,這是事實;但在「五四」之前與「五四」期間,他既無激進舉動,也無鼓動學生運動的言行,也是事實。那麼為甚麼眾多的回憶文章還會不約而同地將他與「五四」掛上鈎呢?撇開巴黎和會這一導火索事件不論,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可說是關鍵。梁漱溟在前面提到的文章裡還說到,在推動五四運動的諸多人事因素中,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樹人四人和《新青年》所起的作用最大。雖然諸位先生的任何一項工作,蔡元培皆未必能做,但如果沒有蔡元培,他們卻可能壓根就沒有機會聚攏在北大,因而也就沒有發抒的機會。同時還必須注意的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雖「無所不包」,但卻有少為人知的傾向,亦即偏袒新派的特點。這從他一方面態度決絕地回擊林紓的指責,一方面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序的破舊與立新中不難看出。陳獨秀細行不檢,常予人以口實,在校內與校外都有人嫉恨,但蔡元培卻多方為之辯護。

蔡元培在北大支持甚至親自發起參與各種社團與組織活動,包括進德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新聞學會等,這也多有人言及。雖然如講演團、新潮社、新聞學會等組織裡不乏社會活動與政治運動的活躍分子──更不要說「五四」後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但若據此即說蔡元培對「五四」有直接作用,仍屬牽強:蔡的原初用意,本在體現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路,並藉以改變師生「奔競及遊蕩的舊習」,至於後來的事態發展,只能說是「無心插柳」—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些,可說北大至今仍保持社團林立的活躍氛圍,依然是蔡先生開創局面的延續。
歐戰結束,蔡元培的興奮和激動與知識界並無二致,在天安門的慶祝大會上,蔡元培演講了《黑暗與光明的消長》(11月15日)和《勞工神聖》(11月16日)。此時的蔡元培,無疑是當時無數陶醉在對中國前途充滿幻想的人群中的一員,期望既殷,失望愈烈,自在情理之中。這可以說明「五四」前他站在愛國學生一邊的原因。
據當時供職於外交委員會的葉景莘說,無力對抗並改變準備在和約簽字的政府時,時任外委會委員長的汪大燮親自坐馬車赴東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電內情告知蔡元培。蔡隨即電招學生代表於家中會議。原定於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遊行,這才改為提前到5月4日──否則,五四運動將可能以「五七運動」載入史冊。
但隨後事態的急轉直下,顯然超出了蔡元培的意料。基於愛國熱情的「五四」遊行示威活動因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和三十二名學生被捕,迅速演變成學生與政府的對抗。這種結果大概既出乎蔡元培的意料,也使他陷入雙重的兩難處境:同情並理解學生的放棄「讀書」,全力投入「救國」的選擇,隨後也採取了全力營救、保護學生的積極行動。但無論就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的個人性情氣質而言,還是依其至死不易的「學術救國」「道德救國」(蔡臨終遺言)之理念來說,他都不贊成,甚至反對學校與學生直接介入政治鬥爭。這種藉助文化啟蒙和教育救國以實現其經世濟民理想的理念,來源於對晚清以降的中國歷史積弊的理解。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有這樣概括性的描述:「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故主張學生「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此意早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反思結論中有過表述:「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正是由於這種思路,我們說蔡元培屬於嚴復、張元濟、張謇一類從文化和實業着手的人物,而區別於康、梁和孫中山這樣看重政治行動的人物。因此,很難說蔡元培如同康、梁領導了戊戌變法,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一樣,策劃或領導了五四運動。

在應對政府一方時,蔡元培也面臨着兩難之境:「五四」後,政府發佈了口氣強硬的訓令,「通令各校對於學生當嚴盡管理之責,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即立予開除,不得姑寬」(教育部183號訓令),作為國立大學校長,理應遵守執行;而另一方面,蔡元培一向「痛惡官僚」,對應付官場文牘、仰人鼻息的苦役早已不堪忍受,加之此次學生運動雖然「激而為騷擾之舉動」,但畢竟出於「愛國熱誠」,於情於理都無法採取政府明令的高壓舉措。所以,處於政府與學生的對峙之間,「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陷入進退兩難處境的蔡元培,實在也沒有比辭職更好的選擇。
但在辭職之前,營救被捕的三十二名學生出獄,不僅是運動得以繼續和社會各界加盟的重要原因,也是校長的分內要務。據曹建說,蔡元培於「五四」當晚,在三院大禮堂安慰了束手無策的學生後,徑赴段祺瑞平日敬重的一位孫寶琦老前輩家中,見其面有難色,「先生就呆坐他的會客室裡,從下午九時左右起一直過了十二時以後不走」(《蔡孑民先生的風骨》)。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裡也說:「蔡先生事先雖曾勸阻學生的示威行動,但事後卻完全站在學生方面,抗拒摧殘學生的壓力。對於釋放學生一事,奔走尤力。」5月7日,蔡元培和各校校長答應警察總監吳炳湘所提出的不參加國恥日群眾大會和立即復課兩項要求後,被捕學生被保釋出獄。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5/16/010116816.shtml